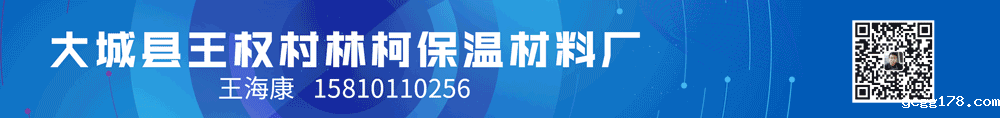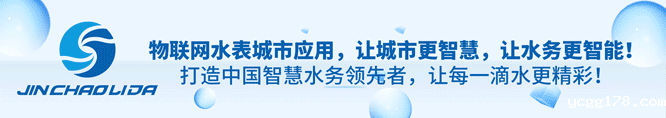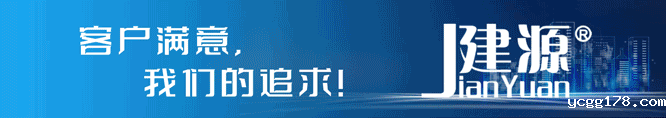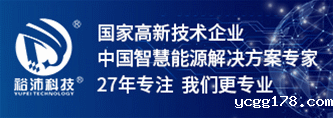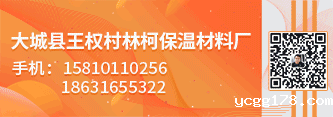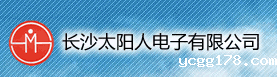“我们乡的生态优势非常明显,老百姓除外出从事建筑业之外,基本上都是从事乌兔养殖、竹木种植等,农业用水问题直接影响到群众收入,事关重大。”通贤乡党委书记丁焱志告诉记者,当地基本上靠农田水利设施解决农业灌溉用水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通贤村为代表的几个村子就在破解农田水利设施管护和管水用水难题方面作出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时光回溯到1989年。当年,通贤村为解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水利设施“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的矛盾,成立了村级水管服务组织,统一管理全村水利设施,由村水管服务组织聘用专兼职水管员,负责统一调配全村水量,计收水费粮。随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事实也证明,这一举措在解决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理、统一调配用水、节约用水、适时灌溉等曾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时移事异。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新情况的不断出现,这种依靠行政命令管水的方式弊端日益凸显:由于产权不明,责权利不清和透明度不够等原因,致使农业水费计收逐年减少,低潮时实收水费仅占应收额的30%左右,村级水管服务组织逐渐陷入有名无实的窘境,这对一个人均只有0.36亩耕地的村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困则思变。2001年11月,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通贤村成立了由农民自行决策产生的农民水利协会。协会成立后,首先采取行政划拨的形式,将村里的一座小(二)型水库、6条陂圳和23公里渠道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全部划归协会,由协会全权负责全村水利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统一负责全村水利工程的调水、配水、用水、节水和收费等,从根本上解决了困扰水利设施管护的产权不清和管护主体不明的问题。
管护水利设施的钱从哪里来?这是协会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贤村根据“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通过民主听证等形式,确定每亩田灌溉用水和村民生活用水(浇菜等)的收费标准。今年,村里每年每亩收费12元,生活用水每人每年1元。为了扶持水利协会的运作,上杭县还对每亩田补贴10元钱。
“我们村水费基本上都收齐了,加上政府补贴的6200元,一共将近15000元,基本解决了水利设施日常管养经费问题。”通贤村党支部书记黄云华告诉记者,为了管好村里的水利设施,村里选聘了6名水管员,而且水管员及其管养的具体水利设施每年都要公开招标、公开竞争,以起到切实效果。
作为水管员,要负责水利设施的日常巡查、管护、三天内能够解决的小维修等等,每月工资一般只有一两百元。一旦遇到大的水毁需要修复时或是新建农田水利设施时,则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由村民筹资、投工投劳或者是向上申请专项维修资金。
“以前水利设施建了也就建了,平常基本没人管,跑冒滴漏严重,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发挥不了作用,现在管护已经形成制度化、常态化,虽然收的钱不多,但能保证正常用水,受益面很广。”谈起成立水利协会前后的变化,通贤乡水利站站长阙吉松说。
变化不仅仅是这些,常态化管养带来的水利设施条件的改善,也让通贤村彻底消灭了耕地抛荒。村里的马湖田、牛粪沟大约有150多亩山田,由于灌溉跟不上,一度抛荒。前年,村水利协会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由会员集资和投工投劳筹资11万多元,并向上级争取配套资金4.9万元,修通了1公里多的标准化渠道和配套的防洪沟并正常管护后,全部复垦成为良田。
目前,通贤乡13个建制村全部成立了水利协会,会员达3923人(户)。2011年,全乡实收农田水费8.27万元,占应收水费的97%。同时,因为明确了水利设施的产权和责权利,当地群众建水管水用水的积极性大为提升,一个个创新不断涌现:
位于上村村的上村水库以前因为没有明确产权,村里不仅没能从中拿到一分钱收入,每年反而要倒贴1000多元的水库管理人员工资,几乎成了包袱。村里成立水利协会后,水库划归协会所有,协会立即对水库进行公开招标,由私人租赁经营20年,每年租金4000元,原来的包袱成了村集体收入的一个新增长点。
有人管护后,水利设施的作用得以很好发挥,大东村群众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只拿到上级3万多元补贴的情况下,村民集资、投工投劳5万多元,建起了1公里多的下坑陂渠,灌溉农田100多亩;通贤乡仅今年投入兴修水利的资金就达到600多万元。
打着手电“守水”,水放到田里后要时刻盯着,防止别人私自扒开渠道“偷水”;因为争水,闹纠纷甚至打架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在通贤乡大东村村主任阙庆贤的印象里,以往灌溉农田时的记忆基本上都是灰色和不愉快的,而这一切都随着村水利协会的成立烟消云散。
“水利协会成立后,一方面是水利设施有人管了,保证了水渠、水圳等处于完好状态,随时可用,另一方面少数几个人专门管水,保证了用水秩序不说,还把大多数村民都"解放"出来, 更多时间去发展生产。”
阙庆贤家里有两亩半的水田,村水利协会没成立之前,一到用水季节,老阙总会紧张起来。因为没有专人管水,争水甚至偷水事件时有发生,一开始放水,他都要去田里盯着、守着,“经常是打着手电筒、带着被子和蚊帐到田里看水,不看的话,你前脚走可能后脚就有人把水放到自己田里去了。”
自从水利协会成立后,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现在灌溉用水可以说是“有条有理有先有后”,用水全部由水管员统筹安排,彻底改变了过去“一人一锄头”的用水方式。 阙庆贤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水利协会虽然花钱不多,但确实是"解放"了很多群众,真是花小钱办大事!”
“有收费就有约束,就有节约意识,水利协会向用水户收取水费,虽然钱不多,而且政府还有补贴,但毕竟还是收了钱的,这对于村民节约用水是很有效果的。”大东村党支部书记、村水利协会副会长阙长星认为,成立水利协会后,村民们的节约用水意识和具体行动都显现出来了。
阙长星介绍说,以往一方面由于农业用水不要钱,另一方面也因为没有专人组织,所以灌溉农田时“你挖一下、我挖一下”的情况比较突出,往往会导致大水漫灌,宝贵的水资源白白浪费了也没人心疼。
成立水利协会后,经过几次听证,村里灌溉农田的费用已经由最初的每亩5元涨到今年的每亩18元(其中今年政府每亩补贴10元),虽然钱并不多,但“有收费大家就会心疼”,现在一家的田浇完了大家会主动去浇另一家的,浪费水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无论是从水利设施管护,还是从解决农业灌溉问题和节约用水等方面来说,水利协会都是符合农业、农村实际的一项创新。” 阙长星很有感触地说。
俗话说,水是农业的命脉。如何趋利避害,让宝贵的水资源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历来是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农民十分关注的问题。通贤乡的实践说明,农田水利不仅要“兴修”,更要“管养”。
与兴修水利相比,农田水利设施的管养问题还算是比较冷门的话题。但管养到位与否直接决定了农田水利设施寿命的长短、作用的大小,进而从根本上影响到农民的收入。
“以往是年年冬修水利,但一些小的水渠、水圳经常建好就没人管了,没过多久破的破、堵的堵,又只能"靠天吃饭",还浪费钱财。”通贤村一位老农这样抱怨以前的水利设施状况。
而这一切,都随着水利协会的成立得以改变:因为有人管护,水利设施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平均使用寿命延长了两三倍,避免了资金的浪费和重复建设;因为有人管护,争水、抢水、守水这些带着心酸和无奈的字眼成为历史名词……而群众和政府每年付出的也仅仅是一亩十几元的投入,真可谓一个小小的支点撬动了一个曾经沉重而又不得不背负的大包袱。
当然,不仅仅只是在通贤乡,整个上杭县,以农民水利协会为组织形式的民间管水组织已全面铺开,完备的水利设施为上杭跻身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综观通贤乃至整个上杭的养水管水实践,不乏很多创新和亮点,但记者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地的大胆放权,将水利设施的所有权划归水利协会,使水利设施名正言顺地成为群众自己的财产,从而使水利设施养护由“要我管”变为“我要管”,彻底解决了以往水利设施管养基本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被动局面,也避免了不少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问题。这种放权的思路不仅对于水利,对于类似领域的管理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0年前我在漳州驻村采访时看到的情形,依然十分清晰。
在一个沿海乡镇政府大院的旁边,一栋两层小楼,崭新气派,上面挂着镇文化活动中心的牌匾,上班时间却大门紧锁。我要求进去看看,镇干部有点不好意思地开了门。室内的乒乓球桌上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哑铃等健身器材杂乱地堆放在墙角,图书室没几本像样的书……镇干部告诉我,活动中心是好不容易筹资30多万元建成的,初衷是为了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由于没专人管理,缺乏日常维护,“好事没办成,还浪费了资源”。镇干部语带无奈。
其实,10年后的今天,这种现象也并不鲜见。在一些农村,农家书屋成了摆设,有时甚至大门紧锁,图书的借阅率很低;文化活动中心成了棋牌室,娱乐设施堆放在墙角,人气最旺的就是麻将桌;村里的体育健身设施“缺胳臂、少腿”,村民都不知道找谁修;水渠坏了、路灯不亮了,往往没人管……投入不少资金建设的惠民设施,因为管理不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着实可惜。
俗话说,三分建设,七分管理。长期以来,农村公益设施推行的是一种“公建公管”的管护模式。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农村公益设施的不断完善,这种模式管护的难度越来越大,效果越来越差,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要抓好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更重要的是探索、创新出一整套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不仅关系到设施功能的发挥,更关乎现代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加强,关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然而,管理比建设更加不易。一是得解决人的问题。传统的“公建公管”模式,在现实中往往沦为“人人都有份、人人都不管”。要解决农村公共设施的管护主体问题,南平推行的“八大员”制度可作借鉴。通过“乡聘村用、规范管理”,明确专人管理,可以专兼职结合,并进行相关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二是得解决钱的问题。除了村民交费外,公共财政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对农村公共设施的管护加大补贴力度。试想,如果上杭通贤乡在水利设施管护方面缺乏财政投入,这个实践就很难成功。每亩补贴10元,虽然政府出的钱不多,但这种有限的公共财政支出却带动了各方面的投入和重视,进而把一件原本看似很难的事情办成了。